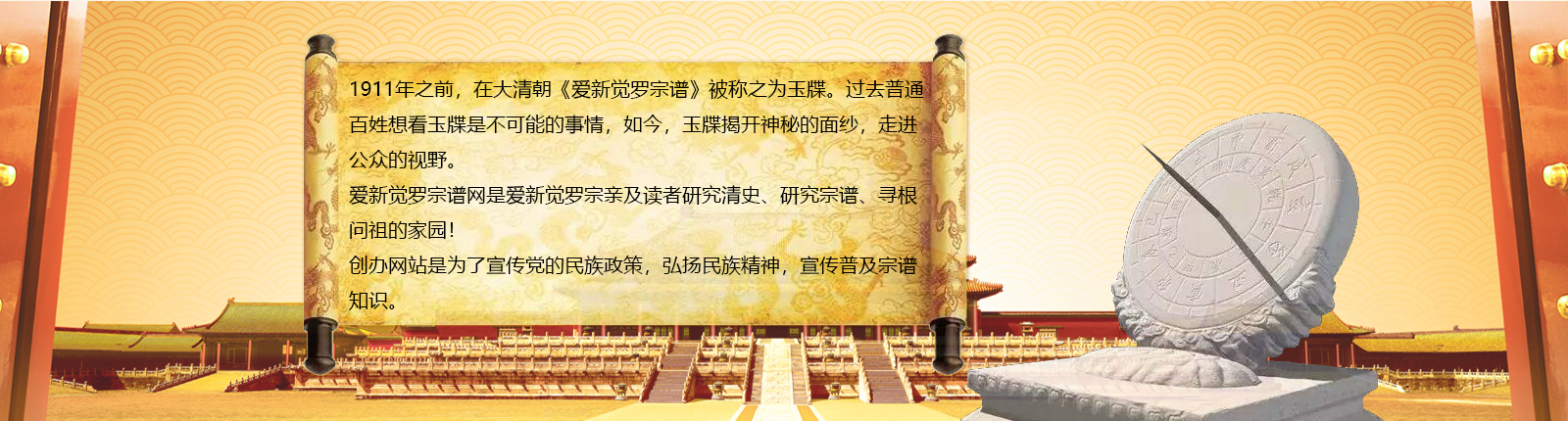


文:张德玉 李恕 王桂红
自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肇造大清丕基以后,女真(满族)的社会组织内部即发生了巨大变化,建立了八旗制度。八旗制度是在原有女真人社会组织牛录的基础上,进行军事、政治、氏族重新整合,使女真社会由原来的各氏族部落的分散状态,逐渐凝聚成为新的女真人群体。这种新的社会军政组织结构制度在皇太极时期得到进一步完善,建立八旗满洲、八旗蒙古、八旗汉军,推动、促进和保障了后金政权乃至大清王朝的建立与稳固。而且,在原有降金汉军基础上,接纳“三顺王”“来归”,在后金社会内产生一个庞大的八旗汉军群体。清入关后,八旗汉军与八旗满洲、八旗蒙古一同拨往各处战略要地驻防。经过长期满汉民俗文化交往交流,促成八旗汉军民俗文化的形成。本文以八旗汉军家谱为研究对象,从清代八旗汉军民俗文化形成的渊源、文化要素及特征诸方面,对八旗汉军民俗文化的形成与实质进行比较研究。

1八旗汉军的构成
孔有德、耿仲明、尚可喜“三顺王”投降归附后,清太宗没有打乱他们原来的军事编制,而是原封不动地继续让他们统帅,给他们以种种优待,因而得到了广大汉兵的拥护,并心甘情愿地为后金政权效命。
宏图大略的清太宗皇太极,更是深谋远虑,慧眼独具。他清醒地看到,“三顺王”统帅本部汉兵,是三支不可小觑的战斗力量,比将汉兵分散到满族各旗管理要更为有利。汉兵既谙水战,又习地战,更习火器,非八旗满洲兵可比。随着争夺全国政权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深入,单靠八旗满洲兵远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。因此,打破民族畛域,充分发挥汉兵作用,使其为国效力,是进军中原、定鼎北京、一统华夏的重要保障。于是,天聪七年(1633)七月初一,太宗下令,将分隶满洲各旗所属汉人壮丁,每十名抽一丁披甲入伍,共得汉人兵丁1 580人,组成一旗汉兵,由汉官马光远统领,用黑色旗帜。自此,汉军旗正式始建。
崇德二年(1637)七月,清太宗皇太极又进一步组建汉军,将一旗汉军分作左右翼两旗:以石廷柱为左翼固山额真,马光远为右翼固山额真,同八旗满洲一样编壮丁为牛录,两汉军旗旗帜均用黑色。崇德四年(1639)六月,太宗又分二旗为四旗,每旗设牛录18员,固山额真1员,梅勒章京2员,甲喇章京4员,任命马光远为正黄旗汉军固山额真,旗用蓝色,以黄色镶边;石廷柱为正白旗汉军固山额真,旗用蓝色,以白色镶边;王世选为正红旗汉军固山额真,旗用蓝色,以红色镶边;巴颜为正蓝旗汉军固山额真,旗用纯蓝色。按清制,每一牛录以百丁左右为满额,一旗含牛录18个,共计1800丁左右。四旗合计7000余兵丁。
崇德七年(1642)六月,清太宗病逝的前一年,皇太极最后将四旗汉军重新改编定制为八旗,正式定名称为八旗汉军,旗色、名称、额真章京官员的设置,一如八旗满洲之制,唯一不同的是,八旗汉军旗主固山额真由皇帝亲自任命撤换,并且不拘时限,而八旗满洲的旗主则是世袭。八旗汉军旗制确定后,皇太极任命祖泽润、刘之源、吴守进、金砺、佟图赖、石廷柱、巴颜、李国翰八人各领一旗汉军,是为八旗汉军固山额真。同年八月,“三顺王”孔有德、耿仲明、尚可喜同沈志祥奏请“以所部兵随汉军旗下行走,上允其请。”[1]4“三顺王”所部汉军虽然没有正式编入八旗汉军,但为八旗汉军之一部分。自此,清太宗终于完成了八旗汉军的创制,使八旗汉军成为大清皇朝功勋卓著的有生力量。

2八旗汉军民俗文化的形成
八旗制度是后金(清)在不断发展壮大过程中日益完善的一种社会军政组织体制,皇太极时期完成了八旗汉军的组建,使后金政权进一步空前强大。八旗汉军的组建不仅使大批汉人归于一统,而且形成了独特的八旗汉军民俗文化。因为自太祖时“俘掠辽沈之民,悉为满臣奴隶”[2]39,大批的汉人或是被俘,或是被掠,或是逃入。据史籍记载,仅宽甸六堡内徙强迫六堡汉民迁回内地时,即有6 万余汉民逃入建州,被当作“种参丁”,“宽甸新疆居民六万余往逼建州寨,种参卖貂与卖狎”[1]4。这里说的“种参”,就是指今天的园参。万历二十九年(1601)建州女真人就在今新宾种植和经营园参了,实际种参时间可能还要早。据《朝鲜李朝实录》记载,女真人多有妻以汉女,生育子女亦为女真人。这些或俘、投、抓、掠、买而来的汉人,皆作为奴隶被满族人臣役使,成为满族民族共同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及至后金农奴主军事统治集团迁都辽沈大地之后,俘虏的汉人和“三顺王”所部的投附,其人数更达十数万,从而使后金汉人数骤然猛增,远远超过了后金女真人的自然增长。
因而,八旗汉军民俗文化,即在被编入八旗汉军的群体中诞生。八旗汉军民俗文化,主要是在这些投附后金的汉军和被编入汉军的汉人中形成的。因此,八旗汉军民俗文化主要体现的文化内涵、文化特征,也主要表现为汉族文化特质。
八旗汉军民俗文化,是介于汉族传统文化和满族文化之间的一种独特的文化。它主要是以汉族传统文化为组成部分,又吸纳融合了部分满族文化内容和形式,重新组合糅合之后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民俗文化。因其主要成分为汉族文化,又形成与传承在八旗汉军之中,故而名之为八旗汉军民俗文化。

八旗汉军民俗文化的形成,主要通过如下几个途径:
满汉通婚,早在明代女真时期就已大量存在,有许多女真人娶了汉人之女为妻为妾,甚至强与为奴的汉人妻女交而生子,此子亦名正言顺地被视为女真人,这在《朝鲜李朝实录》中多有记载。金启孮老先生在《北京城区的满族》中说,满族姓氏中带有“佳”(家)字者,皆原本是汉人汉姓,加入满族民族共同体后,习满族多音姓之俗,而将原本汉姓之后加一“家(佳)”字或“尔佳”,而变成为满族多音姓,即如东北民间俗称之“老张家”“老李家”一样,即如张佳氏、兆佳氏、李佳氏、黄佳氏等等,竟有80余姓之多,占全部670个八旗满洲姓氏的12%。①参见金启孮《北京城区的满族》“哈喇(hala)和冠姓”部分,沈阳,辽宁民族出版社,1998年。金先生的这个说法,只是对大多数加入满族的汉人来说是正确的,而对少数满族带“佳”(家)字的姓氏而言,尚有商榷之处,不在本文探讨之内。
满族进关入主中原之后,虽为小聚居大杂处,其社会生产生活,却是处于汉族的汪洋大海之中,满族人婚娶汉族人亦禁而有之。甚至可以说是从满族贵族统治者即已开禁了的,如顺治皇帝福临,就娶有汉人妃嫔,其章皇后佟佳氏是汉军旗人,石氏是汉族人,巴氏、唐氏、钮氏、杨氏、陈氏和王氏,虽“氏族及父名不详”,也极可能是汉军旗人或汉族人,清代称为“民人”。[3]459上述是清廷皇室与贵族娶汉军和民人女子的情况,而清代八旗汉军贵族娶满族女性之例证就更多了。如《李氏谱系》之李氏是明代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后世子孙。《李氏谱系》修于康熙六十一年(1722),修谱人是李氏十世裔孙李树德,自十世至十三世、十四世娶进和嫁出女性皆详有记载。满族贵族入关后,李氏老长房支,其八世李率祖之长女,嫁给阿达哈哈番本旗步军协领张姓之子;十世李林盛,顺治乙酉年袭父拜他喇布勒哈番,戊子年授镶红旗汉军都统,其夫人诰封一品夫人吴氏,即御前头等侍卫嘎喇昂邦章京之女;十世李林隆,袭阿思哈尼哈番爵,任镶红旗汉军都统,其妻为觉罗氏内大臣席尔根之孙女;十一世李杰,任都水寺员外郎,娶马佳氏正白旗满洲副都统索尔希之孙女,其次女嫁大学士纳拉氏明珠之孙;十一世李炜娶妻纳拉氏;十二世李建基任佐领,其妻为满洲钮祜禄氏;十二世李敦基,康熙朝武庠生,妻伊尔根觉罗氏;十二世李大均,妻觉罗氏康亲王之孙女;十二世李大基,妻兵部侍郎朱都纳之女;十三世李池,妻纳拉氏,正黄旗侍卫五哥之孙女,等等。上述仅是李氏老长房支在康熙朝娶入满族女性的记载,其未明确记娶入女性族籍者有多少人,尚未统计。李氏老房共五支,上述仅其一支,其余四支未予统计,仅此一支所记,亦可说明问题。
其他如平南亲王尚可喜、吴三桂、耿精忠,清初重臣范文程以及沈阳甘氏,尤其清代被誉为“佟半朝”的佟养性、佟养正(真)的后人佟氏,自清初即与皇族等满族贵族互通婚姻,这已被广泛认知。
再以平南王尚可喜《尚氏宗谱》为例,述其族亲与八旗满洲人通婚的情况。
尚氏四世尚可喜诰封平南亲王,隶镶蓝旗汉军。据《尚氏宗谱》(第六次续修谱)记载,尚可喜有子 33 人,出继长房1人,32 子又生孙 86 人,不过三世,已家大业大成为人口众多“与国同休”的名门势旺的大家族。其家族与满族人通婚情况,自五世至十二世,不完全统计如下:
大房八世维邦,妻那拉氏。二房六世崇坦,妻觉罗氏;七房五世之隆,妻和顺公主;六世崇庳,妻和硕公主;八世维慎,妻宗室氏;维岳,妻牛户鲁氏;维昭,妻宗室氏;九世政麟,妻瓜尔佳氏;十二世其光,妻牛户鲁氏;其源,妻觉罗氏;十三世久恩,妻赫舍里氏。十房十世宗轼,妻舒穆禄氏;宗佳,妻希鲁特氏;十一世昌寿,妻觉罗氏;昌本,妻乌齐格氏;十二世其亨,妻乌齐格氏;十三世久勤,妻和硕郡主。以上仅是在清代乾隆朝以前任有官职娶妻为八旗满洲人者。另外,尚可喜的后世女性嫁与满族贵族者大有人在,“大姐嫁阿里香”,阿里香即是满族人。
以上所举《李氏谱系》与《尚氏宗谱》通婚情况并不是特殊个例,而是带有普遍性。再举例汉军《张氏家谱》,其家族入关前归降后金始祖张士彥,原明朝广宁中军守备,编入正蓝汉军旗。该家谱记载世系起于康熙初年,终于咸丰初年,明确记载与满洲旗人通婚的有20人。《沈阳甘氏家谱》,记载清初到道光时期世系。甘氏在明永乐年间著籍辽东,明末归清,隶下蓝汉军旗。该家谱中的著名人物甘文焜,曾官云贵总督。根据其家谱上记载,隶京旗的五支族人婚姻情况统计,与满洲旗人通婚的有39人,占总数11%。②参见杜家骥《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》,第529-533页,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08年。由此可见,八旗汉军与八旗满洲相互通婚虽然所占比例不高,但具有持续性。
再从驻防八旗满洲家谱看八旗汉军与八旗满洲的通婚情况,以《吉林他塔喇氏家谱》为例。该家族清初定居于吉林,明确记载的婚姻719例,其中,与汉姓通婚为210例,占总数29%。汉姓中,汉军旗人80例,“民籍”汉姓人130例。①参见杜家骥:《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》,第529-533页,北京,人民出版社,2008年,第526-527页。再如《白氏源流族谱》。长白山女真人巴雅拉氏,康熙二十六年(1687)由京城拨来辽宁岫岩驻防,该家谱世系记载到民国十一年(1922),十代人,明确记载白氏男性的娶妻姓氏有:洪(洪雅)、汪(完颜)、傅(富察)、马(马佳)、关(瓜尔佳)、唐(他塔喇)、曹(索绰罗)、赫(赫舍里)、何(赫舍里)、敖(索绰罗)、卾(舒穆禄)、康(赫舍里)、董(栋卾)、吴(乌苏),共14 个满洲姓氏;李、高、刘、张、王、郭、孙、罗、佟、贾、于、孟、周、郝、邓15 个汉军旗或民人姓氏;文,1 个八旗朝鲜姓氏;白(巴耶哈)、李(李雅拉),2 个八旗蒙古姓氏;杨、赵2 个或许为八旗满洲,或许为八旗汉军姓氏;郑、陶、肖3 个姓氏或许为民籍,皆出现于清末民初,而且各姓仅出现1人次。②《白氏源流族谱》男性娶妻姓氏的旗籍、民族身份确定,根据民国十七年(1928)《岫岩县志》,高明东、李文通:《岫岩满族家谱选编》,以及对《白氏源流族谱》的收藏人白树标访谈。
《吉林他塔喇氏家谱》和《白氏源流族谱》皆为清代驻防八旗满洲,与八旗汉军以及民籍通婚的比例高于在京八旗,而且《白氏源流族谱》几乎达到五五比例,充分说明满汉通婚对八旗汉军民俗文化的影响。

清入关前归降后金的汉人被编入八旗汉军,清入关后八旗军队以嵌入式派向全国驻防,处于汉人包围中,但在八旗军队内部,满洲、汉军、蒙古混处。东北地区情况更为复杂,顺治至康熙年间,数量不少的八旗满洲、汉军、蒙古陆续返回东北驻防,同时清政府为移民实边,移民招垦,山东等关内大量汉人移民涌入东北,早期到来者被编入旗籍,满汉文化产生前所未有的相互交流影响。由于清代满族处于政治统治地位,因此,满族民俗文化对八旗汉军影响较大,其中,命名有显著满汉语融合特点。
新宾《尚氏宗谱》记载,该支尚氏本是平南王第三十二子尚达之后裔,原为镶蓝旗汉军,但拨调至兴京副都统下,驻防赫图阿拉,与满族混居杂处,于是,习满俗将汉族尙姓改为满尚姓沙格达氏,并将谱名改为《尚氏沙格达哈拉宗谱》。不仅如此,甚或许多人取了满语名。本谱书载至九世,自二世即名满语名为阿拉密,其各世取满语名者:
二世1人,取满语名者1人;
三世3人,取满语名者1人;
四世13人,取满语名者7 人,满汉名合用者3人;
五世50人,取满语名者39人,满汉名合用者8人;
六世12人,取满语名者9人。
七世以下各世无取满语名者,皆为汉俗名,并以范字命名,而满语名如巴海清、巴图力、哈尔萨、七十一等等。令人感兴趣的是,满汉语合璧命名,如黑福、黑妞、得利之类,既非满语,又非汉名,属于满汉语合用名,从而也验证并反映了命名的汉军习俗文化。
再例如《高佳氏家谱》。高斌,文渊阁大学士,曾祖高名选,努尔哈赤时期归附,是典型的“老汉军”氏族。该家谱第五代,即高斌下一代,大约为雍正末期,乾隆初年,族人中开始有满文名字出现。例如第五代图克善、萨克慎。第五代高文焕的4 个儿子皆为满族命名:观音保、喀宁阿、佛保、千佛保。③该种命名,究竟是否为满语目前尚未有准确定论,但在满族人名中重复率较高。图克善三个儿子中有2子为满语名,果尔敏阿、吉尔敏阿。
再例如《金氏宗族谱书》记载,金氏原籍山东,雍正年迁入吉林,在陈汉军正白旗第五牛录当差。该谱自第七代始有满语人名出现:领催那里吉、领催老格、笔帖式科什布、苏明阿,直到第十代始,满语人名消失。
另外,还有《李氏谱系》《王氏谱书》等许多汉军旗人家谱都有满语命名记载,在此不一一例举。

原本为汉人,由于被俘、投充、来归、掳掠等等,作为包衣阿哈被分配编户到各满族贵族下做奴仆。这种性质的汉人有数万乃至数十万,他们或是单个人,或是一家人,或是一族人,或是一村一屯人,他们中必定有读书识字之人,汉族的民风习俗也必然保持传承着。比如,在佛阿拉城居住时,过年贴对联,就用毛笔书写汉字对联贴于房门[4]。这些汉人在满族之主下生存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,更有一家几代人为奴者。自努尔哈赤时(甚至更早)直至入关后的雍正、乾隆之时,这些汉人在与满族(女真)人的长期共同生活中,必然渐染满族习俗,而当他们由包衣转成汉军后,就解除了奴隶身份,恢复了平民身份,但不是作为普通汉人,即“民人”,而是被编入八旗汉军[5]145。这就是说,凡在八旗满族都统属下的包衣汉人,不论是上三旗,还是下五旗,不论佐领下人、管领下人,还是庄头人,一律遵照这个规定,参加科举考试,这是把汉姓包衣视同汉军处理的最明确的官府规定[5]145。由此,这些转变身份的汉人包衣,就自然而然地将其作为包衣时所习之满族民俗文化,带入八旗汉军中来,从而促使八旗汉军民俗文化的形成。
据正白旗满洲《佟佳氏宗谱》记载,佟氏包衣某姓汉人数代依附“佟老爷”家为仆丁,嘉庆年间,佟氏允其恢复民人身份,但他一家自认为“佟姓”,并以正身旗人自居。后来,这支“佟氏”族人被编入汉军正蓝旗,他将十数代吸纳的满族风俗带到了汉军军营,从生活居处、节日礼仪、丧葬祭祀、婚嫁等习衍汉俗,虽如此,但仍传承着部分满族习俗,如结婚“打下处”、订婚他哈猪等仍习满族习俗,这就彰显了清代八旗汉军特有的满汉融合的习俗文化特征。
正黄旗汉军《张氏宗谱》载,张氏原本为满洲正黄旗赫舍里氏之仆人,嘉庆时被拨至正黄旗汉军,驻防兴京,为兴京副都统辖下额兵。光绪时,张氏家族曾帮一远支张氏光棍抢邻村一张氏寡妇为妻,生一子一女,并记入宗谱。这“抢婚习俗”就是满族传统习俗。
满族汉人包衣,转为汉旗军人,一个最为正当的途径就是“胥隶汉缺”。据《听雨从谈》载,雍正十一年(1733)“包衣汉姓人员归入汉军额内考试”,因而,这些汉人包衣就可以“由科甲出身,胥隶汉缺”[6]17、6,由包衣转为汉军,为汉军习俗文化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八旗制度是清代满族军民合一的社会军政组织,它主要由八旗满洲、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三部分共同组合而成。“编旗即编户为民”[7]142,佐领对编旗之民的婚姻嫁娶、田宅、兵籍、诉讼等项无所不管,佐领就成为了编旗之人户的父母官。人少则编佐领,人多则编旗。此外,还有内务府三旗,其中满族包衣佐领、旗鼓佐领是最早编成的旗籍组织。“有清一代八旗与内务府三旗成员之称旗籍,犹汉人之称民籍”[7]144。另外,万历十一年至四十三年(1583—1615),努尔哈赤初起兵所建立起来的八旗满洲牛录208个、蒙古牛录76 个、汉军牛录16 个,汉军牛录大多是汉人,少部分是满人,而满洲蒙古牛录中也有不少汉人成员存在[7]144。后金初期的征服战争自万历十一年至二十七年间(1583—1599),辽左汉人被杀掠者数十万人。自进入辽沈大地之后,仅天聪九年(1635)、崇德元年(1636)、崇德四年(1639)、崇德八年(1643)四次后金所俘获汉人总计“八九十万之多”,这虽有夸大战果成分,但实际上至少应有三四十万人。后金征伐政策是抗拒者杀,俘者为奴,而归降者则编户为民,即编为佐领下人。这些汉人大部分都被分配给满洲王、公、贝勒等及各佐领官兵为奴,小部分被编入八旗满洲佐领之内,成为满族兵丁。
据《裕亲王府世袭庄头刘氏宗谱》记载,刘氏“一世祖守德公于明季末叶,由山东省某郡始迁于辽东,居抚顺县之塔湾村”,自二世始由“民籍改旗籍”,“隶入裕亲王府充任庄头之差,世袭罔替”,遂为“旗人”。旗人命名不讲究范字,因此,清代刘氏自清代晚期才拟定“十六字排行”范字。《锦州料理庄粮事务衙门陈庄头家谱》记载,陈氏原本长白汉人,明末编入正黄旗满洲,历任九格内管领下世袭庄头,谱系至九世,仅四世有几人命满族人名,余数百人仍为汉族名,在命名上犹如沙格达尚氏一样,满汉习俗兼混。《镶黄旗汉军卢氏家谱》记载,卢氏本山东章丘栖霞汉人,顺治八年(1651)奉谕迁辽东,“拨入奉天镶黄旗汉军”,驻居凤凰城,历任佐领,因长久与旗人为伍,尤其婚嫁祭祀,渐染满俗,如新娘下轿进洞房要跨火盆,以示红红火火,居室南北大炕,炕梢连“万字炕”等等习俗。
汉人投充满族,被编户为满族佐领下人,称为“投旗”,这种投充的汉人无疑也是旗人。
满族贵族为了解决人口少劳动力不足问题,就多收来投充的汉人。有的投充人甚至借满族主人之名护身而逼勒其他未投充的汉人投旗。此外,还有卖身之汉人,投入满族人之下。这些投旗或卖身人丁,既属于奴隶身份,旧俗有所谓“一日主,百岁奴”说法,一人投而全家俱投为奴,并且世代为奴。
据山东等地“闯关东”的汉人家谱记载,这种情形较为普遍。《卢氏家谱》记载,卢氏于顺治十一年(1654)由山东栖霞迁辽东,被拨入奉天镶黄旗汉军;《金氏宗谱》记载,金氏于康熙年间拨民来辽,被编入盛京内务府镶黄旗汉军;《何氏家谱》记载,何氏于“清顺治年间”“毅然出关而东”,“被编入豫亲王依惠佐领下”为庄丁;《王氏宗谱》记载,王氏“维满清以来,我族投入盛京内务府汉军镶黄旗充差”;《镶蓝旗汉军王氏家谱》记载,王氏原籍山西小云南人,明代迁山东琅琊,顺治八年(1651)奉圣谕拨民辽东海城,编入汉军;《安邱王氏族谱》记载,王氏本岳飞后裔,岳飞次子岳雷在其父被难后迁居安丘改姓王氏,清初入军籍,拨至永陵当差;《李朝文子孙宗谱册》记载,李氏于雍正四年(1726)由山东拨民来辽,投入汉军旗;《高氏宗亲谱册》记载,高氏“籍隶山东登州蓬莱县属高家庄处”,于清初“由岛兵投旗”“列入汉军旗籍”,在“盛京汉军镶黄旗第一佐领”下“管理折本房兼户司行走”;《边氏家谱》记载,“边氏乃山西洪童(洞)人”,后拨迁山东任丘小云南,顺治八年(1651)拨民迁居辽阳,“奉皇恩赐闾阳驿镶蓝旗(汉军)当差”;《崔氏族谱》记载,崔氏于顺治年间拨民投充奉天汉军正红旗,落居威宁营,等等。
顺治时下召移民辽东,开垦荒地,一批批奉召移民辽东垦荒的汉人,在此后带地投充入旗籍的人户,多达数万人,远远超过汉军正身旗人人口。

汉军,指以佐领编制纳入八旗汉军的正身旗人。内三旗和外八旗的汉军人数(含人丁及女口),据统计至少当在300 万人以上,“到清朝末年,在盛京将军管辖的辽东,八旗中汉人人丁(包括外八旗汉军、内务府汉姓人丁)的比例,占据全部旗人人丁的将近四分之三,在全部汉姓人丁中,属于内务府的,又占到四分之三以上,也就是说,内务府三旗人丁,占据辽东八旗全部人丁的55%∼60%之间。如果以人口数量计,内务府三旗人口(包括女口)至少当在300万以上,甚至更多”[8]214。这些汉军旗人在与八旗满洲人的密切接触中,自然接受了一些满洲习俗。
当然,还有以其他形式加入八旗汉军的,也带来一些满族民俗文化,对丰富八旗汉军民俗文化产生一定影响。
上述种种,清代汉军旗人、旗下人及其他性质的汉人,如罪犯逃入满族的汉人等等,还有八旗满洲户籍内之佐领下人(或作户下人),自然含有不在少数的汉人成分。这些汉人所传习的部分满族民俗文化,也自然应属八旗汉军民俗文化内容。
有清一代,“只辨旗民,不分满汉”,在八旗中基本上没有满汉之分。《清世祖实录》记载:顺治七年(1650)谕:“八旗汉军,其初本系汉人,有从龙入关者,有定鼎后投诚者,有缘罪入族与夫三藩户下归入者,有内务府、王公包衣拨出者,以及招募之炮手,过继之异姓并随母亲等类,先后归旗,情节不一。”如《张氏宗谱》所记,清初,张氏“我祖等投诚来归”,“世祖入京定鼎燕京,编为汉军正黄旗”,迨八年,“拨往盛京驻防”。如此加入八旗的汉军或内务府三旗的汉人,在清代的社会地位和生产方式基本相同。这与民人相比,在政策上旗民不交产、旗民不通婚、旗民不同法,旗人由旗衙门管理,民人由府州县管理,旗人的身份靠世袭保障,这就有很大的不同。
在旗籍中,内务府所属镶黄、正黄、正白上三旗由皇帝亲自统帅,上三旗下的包衣被束缚在旗地的庄头和庄(壮)丁,大多是汉人。清中期允许大量汉军旗人出旗为民(也有个别八旗满洲人出旗不披甲做闲散的),而内务府的这些包衣却因“皆系内务府世仆”而不准出旗,这人丁数额巨大的包衣,自然有条件染习了满族的民俗文化。
由努尔哈赤创建、皇太极改名的满族发展至后金,最后又入京建立了大清。这些国号更名变迁的同时,与八旗建制的扩充与再编,是同时进行的。清入关时满、蒙、汉八旗共为22.4万人,而汉人加入八旗并未因八旗汉军的成立而终止,此后仍有大量汉人以各种形式加入“旗人”行列。从清入关之初,直至清代中期,在两个世纪中,汉人相继投充满族而被编为佐领下人的不下几百万人之多。当然,投充后又逃亡恢复汉人成分的,约在百万人左右,但留在旗籍内的投充汉人仍有数十万人[9]。这些汉人编入旗籍后,与八旗满洲人就有更多、更直接的接触、交往、联系,也就自然熏染部分满族民风习俗,并将之融于汉俗之中。这种民族间的风俗民情的相互影响和吸纳,既不可避免,也是必然的发展趋势。

3八旗汉军民俗文化的实质
所谓八旗汉军民俗文化,就是汉族文化融入或吸纳满族文化后所形成的文化,它既非完全的汉族民俗文化,又非满族民俗文化,而是以汉族民俗文化为基础,融入了部分满族民俗文化元素,是一种独具特色,有自身形成发展轨迹的文化。
八旗汉军民俗文化内容很多,比如,满族的居住建房习俗“筒子房,蔓枝炕”、妇女天足、饮食习俗、萨满信仰习俗等等,都对八旗汉军民俗文化形成产生影响,辽东地区尤为显著。这里谨以汉军旗香为例,说明八旗汉军民俗文化的实质。
汉军旗香源之于民香,民香源之于唐王李世民征东祭祀阵亡将士的祭奠活动,这一点已为学者共识,毫无疑义。
汉军旗人烧香(简称汉军旗香)是清代汉军八旗人的一种主要祭祀形式,曾广泛流行于满族设立八旗汉军晚期的东北三省,从总体上看,它是民香在清代满旗设立八旗汉军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流变[10]1。清代汉军旗人成员复杂,来自各地,但主要来自山东河北等地。汉军旗香在其发展演化过程中,不断汲取满族和其他各地汉人的祭祀形式、内容,糅合进自己的祭祀活动中,因而形成八旗汉军旗香。
这里先说一下民香。民香是区别于汉军旗香与满族萨满祭祀的一种祭祀活动,主要指没加入旗籍的汉族人的烧香行为。民香香班主要从事祭祀活动,曾经广泛活动在辽宁东部的岫岩、宽甸等地区。
民香活动近于巫神信仰,其娱人功能远大于娱神功能。民人烧香,俗称跳单鼓子,又称唱家戏,还称太平鼓烧香。其功能主要是祭祖、还愿、清宅、驱邪。民香师傅通过祭拜土地、先行请神、请亡魂,神与亡魂不能附体;而满族萨满可以直接请神,神可附体,这与民香不同。
烧香是一种大型歌舞演唱,有唱有舞,间有少量的韵白与说口。香卷唱词以七言为主,上下句结构,亦时有叠句,全部仪节由唱词统领。民香分“内坛”“外坛”,亦称“内路鼓”“外路鼓”。内坛有八个仪节,亦称“八铺”,为烧香中的祭祀部分,是必须演唱的。外坛,亦称“二十四铺”,是烧香中的娱人部分,此部分可根据烧香香主人的意愿和经济状况而有所选择,可长可短。“八铺”分为开坛、搭棚、下山东、开光、闯天门圈子、勾亡魂圈子、安座、送神等八个环节;“二十四铺”分文出、武出。文出即挂匾,每块匾都是配合祭祀内容演唱的一个完整的故事,如《李翠莲盘道》《孟姜女寻夫》《张郎休妻》《汉高祖斩白蛇》《谭香女哭孤》《杨二郎开山救母》《白猿偷桃》《孙庞斗智(法)》《黄氏女游阴》《武王伐纣》《唐二祖征东(唐王征东)》《刘伶醉酒》《珍珠衫》等等。武出即指有对白、有一些情节的小戏及某些武术动作和绝活。武术如《五道捉妖》《勾灶王》,绝活如打刀、滚小鼓、丁霸五鞭、走腰铃等等。外坛穿插在内坛中,武出分散在八大本坛中,而文坛多集中在亡魂圈子过十大山口一节之中。
民香在辽东乃至在东北的长白山区得以广泛迅速发展,有其社会背景。清乾隆朝为了削弱除爱新觉罗氏以外各满族大姓的亲族意识,颁行了《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》,满族故里推行尤为严格,从而使满族各氏族萨满跳神活动受到了一定局限,而使民香活动蓬勃发展。笔者通过田野调查得知,宽甸县烧香(单鼓)艺人祖师杨希春,于光绪甲午年(1894)生于山东省文登县一个单鼓世家,六岁随祖父杨青岩迁来宽甸杨木川镇落户,跟祖父学单鼓技艺四年,长成后因技艺高超,名声赫赫,推为“坛主”,后成为《杨氏香坛》掌门(掌坛)人,今已传至第四代。其他香坛,如新宾东江沿村张明学、木奇水手李氏、东站王氏香坛,宽甸县王氏、汤氏香坛,本溪县于新友香坛、小堡香坛,丹东何忠贵香坛,凤城孙氏香坛,沈阳苏家屯张恩宝香坛,吉林永吉县常氏香坛等等,皆从山东登州、青州等地传来辽宁、吉林。究其原因,即道光以后,清代柳条边弛禁,大批山东、河北等地汉人涌来辽东耕垦采参等为生,从而,将关内香坛技艺传来辽东。烧香由山东、河北等关内各地传入东北,进而传入八旗汉军,形成与汉民不同、更与满族相区别的具有独特内涵的汉军民俗文化,即一种特殊的“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”的满汉杂糅文化。
原始信仰方面,八旗汉军也同满族旗人一样相信万物有灵说,如对古树、大山、大河、灵性动物(如狐狸、蟒蛇、黄鼠、黑熊、刺猬等)等等进行崇拜,甚至也有向古树古洞讨药活动,但主要祭祀活动还是烧香。祭祀供品同民香大致一样。然而,祭祀时比民香要严肃规范。汉军旗香与民香主要区别在于祭祀时有请虎神仪节。笔者清楚地记得,少儿时的笔者,曾晚饭后跑四里地到一张姓人家看烧香。烧香班子是邻村西河掌村的,掌坛人即俗称“神匠”的于长阳。他们烧的就是汉军旗香。于长阳是旗人,但居于何旗已不记得了。于氏香班为张氏汉军族人祭祀烧香就有请虎神跳虎神的动作,只见一人扮大虎(似是母虎),二人扮小虎崽儿,大小虎蹲跃翻滚、大虎背小虎腾挪嬉戏,虽未披虎皮衣,但动作形象,小鼓前后胯下打逗,坛主神匠扮大虎腾挪跳跃,场面活跃欢快。这种请虎神的烧香表演仪节,显然是满族萨满。此外,还有五道驱五鬼的仪节,由一人扮成五道,另有五人扮成恶鬼,五道清宅捉鬼,与民香不同,当源于早期的汉人祭祀。
汉军旗香与民香,与满族萨满祭祀相比较,无论从烧香香卷内容、演唱表演形式,还是从其目的性、严肃性几方面看,都有各自的文化特征,有各自的特点和渊源,因此说汉军旗民俗文化是自成体系的文化。
但伴随清末以后,八旗居住地大量汉民涌入,满汉人口结构发生巨大变化。以辽宁岫岩为例,清末宣统元年(1909),有旗户6 776户,其中:满人 4 136 户,蒙人 340 户,汉军 2 300 户,合计45 984 人口。有汉户13 913 户,外加寄籍(流动暂住人口)150 户,合计112 666 人口。汉户人口是旗户人口的 2.45 倍。[11]17民族人口比重影响风俗习惯取向。清代道光、咸丰以前,八旗满洲人口占多数,汉军旗民俗受其影响为主。但清晚期,不断流入的大量汉族人口带来原输出地汉民文化,形成满汉文化大汇合。民国时期,近现代思想通过新式学校教育输入满汉旗人聚居地,八旗满族民俗文化的主流地位不断式微,而原本以汉文化为基础的八旗汉军民俗文化又重新向汉民文化趋同,逐渐融合一体。(内容来自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11期)
原载于红缨满洲
爱新觉罗宗谱网转载
2024年7月11日
 辽公网安备 21010302000807号 辽宁满协(2022)第7号
咨询电话:18540068988 13998815316 邮箱:haiqing9876@163.com 官方网址:http://www.axjlzp.com
爱新觉罗宗谱网知识产权证书 版权所有Copyright © 2016 qingchao. All Rights Reserved
辽公网安备 21010302000807号 辽宁满协(2022)第7号
咨询电话:18540068988 13998815316 邮箱:haiqing9876@163.com 官方网址:http://www.axjlzp.com
爱新觉罗宗谱网知识产权证书 版权所有Copyright © 2016 qingchao. All Rights Reserved